宋朝时,朱熹在《家礼》中依据当时的生活方式建构起了一个普世性的“家”、一个理论形态的生活世界。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构建了一个生活世界(家),突出了人的情感体验性质(敬),实现了人生的最高审美境界追求(乐)。这个结构完备、操作简便而内容丰富的极具实践智慧的礼学体系,是中国礼学发展的高峰和标志。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饭桌上需先等长辈先动筷”“双手接别人递给的物品”……诸如此类,这些礼仪仍浸透在当下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今天,朱子家礼是否还有其价值?在家庭生活的琐细中,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礼仪,看到一种美。
阅读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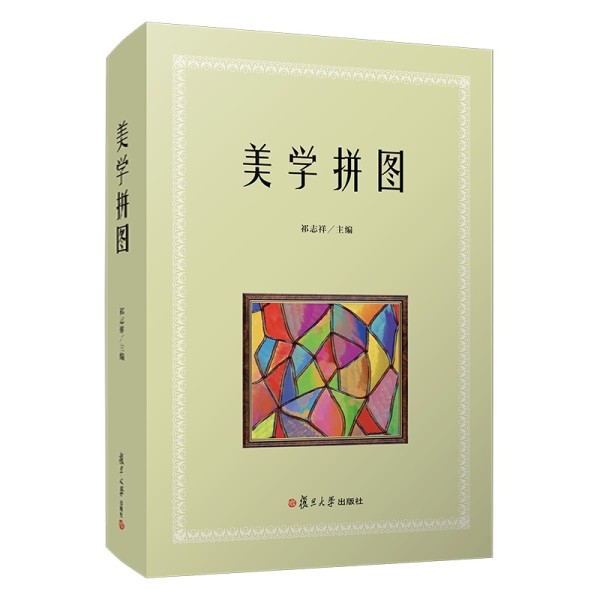
《美学拼图》
祁志祥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2017年以来第九届上海市美学学会代表性论文的汇编。
这是一次“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学实践,一次没有彩排的学术会演,一个随机应物的美学拼图,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探寻。
四年一度的学会会员成果结集,将上海众多高校和机构的优秀师资聚合在一起,成就了难得的豪华作者阵容。
充当章节的论文曾在各种名刊发表过。
本书也是学会四十周岁生日的献礼文集。它记录了上海美学家的奋斗踪迹,体现了老中青学者的学术接力,为中国当代美学画卷献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朱子《家礼》的生活世界
朱子《家礼》是对中国传统礼学思想和礼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家礼》早在孔子编撰的《仪礼》之中就有所呈现。如《士冠礼》《士昏礼》《丧礼》等。又如《礼记》中有大量关于婚丧嫁娶、宗族制度、社会风俗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南北朝时期徐爰的《家仪》、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及隋唐时期的书仪类作品等。这些都成为朱子《家礼》的重要思想来源。
宋型家庭的转型,“礼下庶人”,推进了礼的普适化进程。学界普遍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发生重大转变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由“汉唐型家庭”向“宋型家庭”转变。而“宋型家庭与以前形态家庭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功能由原来的选官、婚配转变为敬宗收族了;或者可以概括地讲,由政治型转变为血缘型了”。宋型家庭是中唐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学术以及礼俗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儒学的复兴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主旋律。面对“礼崩乐坏”混乱局面,宋代士大夫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雄心和气魄,肩负起了整饬风俗与教化百姓的使命,从而开启了因时制宜的以弘扬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精神改造整个社会“崇化导民”的文化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家”“国”一体的认同达到了高度一致,由此,宋代家礼的编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家礼、乡礼、家训、家范之类的著述大量出现。
其中朱子《家礼》参透最为深刻,适应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趋势,成功改造了传统家礼,剔除了传统家礼中的政治因素,设计了一套新的血缘型的家族制度,可谓集传统“家礼”之大成。因此也就成为宋元以后中国传统(也包括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家族制度的基本教科书或模板。如《郑氏家仪》、从《家礼》到《明集礼》、从《家礼》到《茗洲吴氏家典》、从《增损吕氏乡约》到《泰泉乡礼》等,无不体现着《家礼》痕迹。
朱子《家礼》的基本框架如何呢?依据目前《家礼》文本的条目而言,全书由《通论》和“四礼”(冠、昏、丧、祭)组成。朱熹在《家礼》中主要建构了一个以人生为本体的生活世界。其中“冠礼”“昏礼”是对生者的礼仪,而“丧礼”“祭礼”是对死者的礼仪。人生的两个节点就在于“生”和“死”。如何生、如何死也就自然成为人类永无休止的追问主题。朱子《家礼》充分改造中国传统礼仪之后正是把握住了这一永恒之主题,从而建构了一个以人生为本体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美学系统。
2
朱子《家礼》的美学之维
礼学的美学维度,正在于礼学的人生化。正如《家礼》把握住了人生世界的生与死两个节点,实际上也就使礼学渗透到了人生方方面面的包括人的生之滋味与死之回味的全体人生美学建构之中。人生之物质层面来源于自然万物,但精神层面却来源于天人沟通之心灵,更重要的文化层面则来源于天时、地利、人和、事宜的互动建构之中。
朱子《家礼》构筑的一个生活世界,立足于人的自然本真的情感,而礼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情,一种沟通天人、心物之情。这种情的原则是“中”“中和”,尤其是情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特性的“中和”。这种情究竟如何物态化或形象化呢?
在《朱子家礼》中,朱熹通过“四礼”将其具体化、形象化并秩序化。例如朱子《家礼·通礼》中的“祠堂”将这种情场所化了。场所化使得体现人生意蕴的“四礼”形象化,并逐渐建构成人们心灵皈依或寄托的场所——家的象征性符号。同时这种场所化的情也具有了浓郁的美学性质。且看朱子在“祠堂”词目下的论述。
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着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此则注释至少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祠堂”本是“祭礼”篇中的,但朱子将其中祭神的性质改为了祭祖,突出并强调了家或家族“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的宗旨。由此,“祠堂”成为“家礼”的大本或中心。并作为通礼之首统领“四礼”。其二,“祠堂”是“四礼”根据。其三,“祠堂”概念的使用,在于现实社会的要求,这就是“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其四,就“祠堂”的制度而言,朱子也力求大众化、生活化或从俗化(“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朱子《家礼》中的“四礼”实际上就是展示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美的夙愿。包括美的标准、美的原则、美的对象、美的生成、美的境界等等。也就是说,礼乐人生是朱子《家礼》美学的核心精神!
3
《家礼》美学的当代价值
当代美学研究越来越倾向对于生活本身的美学问题的探讨,如生活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休闲美学、时尚美学等等,无不展示着美学当代意义的真实呈现与多元深入。生活美学作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方向之一,家庭美学无疑应该是生活美学核心价值。当代家庭美学如何建构也必将显现出其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双重的价值和意义。在此,仅就朱子《家礼序》来讨论家庭美学的当代价值。
朱子《家礼序》全文如下: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国同构”为核心建构模式的身份社会。“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家”既是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元素,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公共事务展开的基本场所。在“家”既有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景观,也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理想追求萌芽与初生。“家”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生存目标和归宿,更是以个人的审美方式建构的场所。因此,朱子对《家礼》的建构与完善付出了特别的心血,其思想境界影响深远。
家庭美学中最为关键性的就是“礼”。而礼有本有文。礼之本、文,乃从宇宙运行之大势论及礼之渊源与本质,突出了家礼的自然性生成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道法自然”思维的总特征。“礼之本”亦即“礼义”属于“礼义学”的范畴,重在考察“礼”的本质问题。而“礼之文”亦即“礼仪”属于“礼仪学”的范畴,重在展示“礼”的现象问题。
荀子曰:“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天地之为“本”,所重在于它是万物生存之超越性本原;先祖之为“本”,所重在于它是血缘性的族类始源;君师之为“本”,所重在于其是礼乐创制道德教化之根源。祭祀是“礼三本”的集中体现,与天地、人生、文化、政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家礼序》涉及的重要美学问题有:
(1)礼本与仪文: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体与用,理一与分殊。
(2)古礼与今俗:时变,损益问题,因时制礼,礼时为大,古今之变。
(3)习礼之态度: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质与文。
(4)家礼之宗旨:从修身齐家之道、到谨终追远之心,直到崇化导民之意,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图。
《家礼》的旨趣在于“可行于今”的礼仪,注重的是现实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应用,因此在整个体系上,特别注重的是礼在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地位等各类人群的可操作性问题。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