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盗窃罪的既、未遂及与相关罪的区别
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的最高刑罚可达到无期徒刑。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法律常识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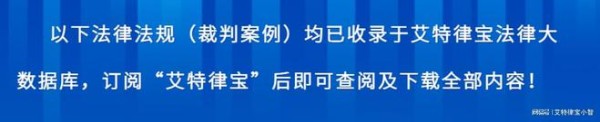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二)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盗窃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盗窃罪既遂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4月2日,法释〔2013〕8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
盗窃罪的既未遂标准,向来众说纷纭,大致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损失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诸多论点,表明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里不一一赘述。最具代表性、最流行、最为大家所接受的主要是失控说和控制说。失控说基于法益保护的角度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即控制为标准,凡是盗窃行为已使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实际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的,即为盗窃既遂;而财物尚未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的控制的,为盗窃未遂。控制说站在犯罪是否得逞的立场认为:应以盗窃犯是否已获得对被盗财产的实际控制为标准,盗窃犯已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既遂;盗窃犯未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未遂。由于物主丧失占有或控制并不一定等于盗窃犯实际占有或控制,故二说在某些案件适用上会导致不同的认定结果。应当说,二说各有千秋,不过,控制说基本上是通说,也更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既遂的一般规定。
明确了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标准是控制说,并不意味着就搞定了一切问题。实际上,由于盗窃对象的不同,盗窃行为使用的手段不同,以及盗窃时的环境及条件的不同,在面对千差万别的具体盗窃行为时,判断所谓取得“实际控制”仍是个极为复杂棘手的问题。总结司法实践,结合社会一般经验和常识,一般有以下几种考虑因素及常见判断类型:其一应考虑被害人对物的控制权范围的问题。例如盗窃工厂的财物,工厂的权利范围就是整个厂区,在工厂内盗窃工人的个人财物,工人的权利范围就是本人的衣柜、工具箱等。一般情况而言,盗窃分子将财产盗离被害人权利控制范围,也就标志着控制并非法占有了财物,构成盗窃既遂。但是,由于控制范围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复杂性,实践中应加以区别对待。至于在无人监控或无特定控制区的室外,将财产移离原处即为既遂。其二应考虑被盗对象的特点。被盗财物的性质、重量、体积、形状等不同,盗窃分子行窃时控制其财产的难易程度就会不同,因而认定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可能不同。例如窃取货币,一般只要窃离原处,即为既遂,而其他财产,则要脱离一定控制范围,才属既遂。一般来讲,如果是不能随身携带之物,应以窃出控制范围外为既遂,如果是轻便容易随身携带之物,应以将财物移离原处隐藏于身或随身携带的包内为既遂。体积小、重量轻可随身携带的财物,只要窃离原处或携带身上,即可认定既遂。如行为人将车间或办公室贵重轻便之物放到自己的包内,或隐藏于室内或室外他人不知之处,使原财产所有人失去控制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盗窃分子已经实际上对该财产享有支配、处分权,即构成既遂。而对于体积大或沉重之物,只有将其移离于原物的有效控制区外,盗窃分子才能实际控制而成为既遂。
常见的类型有:
1.扒窃的既未遂。一般认为,只要行为人一把被盗财物从原控制人的衣袋或提包中窃取出来,就意味着原控制人对财物的控制丧失,同时盗窃行为人获得对所窃财物的控制,为既遂。反之,如果扒窃者着手犯罪后没有能达到这种程度,还没有把财物从控制人的衣袋或提包中拿出来就被抓住,则属于未能获得对财物的控制,系未遂。
2.入户盗窃的既未遂。由于物主对户内财物具有实际的控制权,一般认为只有盗窃行为人将所窃财物带出户外,方成立既遂。在财物被带出屋外之前,很难说盗窃行为人已经排除了被害人的控制而取得自己对被盗财物的控制。当然这也存在例外:如是货币到手即为既遂;如果是雇用工人因其有权利自由出入主人的房间,所以雇用工人乘主人不备,窃取财物置于自己支配之下,虽然没有将财物带出屋外,同样可以成立盗窃罪既遂。另外,还要根据房屋的具体情况判断何谓屋外,如果是城市的公共楼房,屋内自然是指自家所能控制的门内,而门外的楼道自然不属其可控制的范围,因此这种房间的屋外自然是指门外。而在广大农村,每户住宅除了有房屋以外,还有一个自家的小院,这个小院也是主人的控制范围,这种情况下,盗窃行为人如果只是把财物窃到房屋外,还没有出小院的范围时,一般也不能认为盗窃行为人已经取得了实际控制,所以带有院子的房屋的“屋外”一般应指院子的外边。
3.店中盗窃的既未遂。商店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其门口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出入的,故商店对财物的合法控制范围不能以门口为标准。柜台销售的,物主对财物的合法控制范围以柜台为限,只要行为人一将财物窃出柜台即标志着行为人控制了所窃财物而成立盗窃既遂。超市型的商店,顾客可以在超市允许的范围内随便拿取商品,但是这个区域都有一个警戒线,行为人一旦把财物窃出这个警戒线,就可以认为行为人已经控制了所窃取的财物,成立盗窃既遂,无需带出商店的门口。但是如果是商店的非营业时间,则商店对其财物的控制范围就为整个商店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盗窃行为人只有把财物窃出商店,才标志着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了所窃财物而构成既遂。
4.企事业单位等有人管理区域内的盗窃既未遂。从原则上讲,盗窃行为人避开管理人的警戒,把所盗财物带出被管理人有权利控制的区域即为既遂。但是因为警戒管理有严有松,这当然会影响到盗窃的既遂未遂,并且被盗对象的形状有大有小,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既遂未遂的时间。例如,盗窃行为人在一家工厂里盗窃工厂的财物,如果财物体积小便于藏在身上,一般来讲当行为人将财物藏在身上时就已经盗窃既遂。但是这还要根据工厂的警戒和管理的具体状况而定,如果工厂的性质比较特殊,出入门口都要经过严格检查,这种情况下,盗窃行为人在厂内窃取的财物虽然已经藏于身上,但是在没出门口之前,仍不能认为已经取得实际控制。另外,即便是工厂的门口并非严格检查,比如搜身,但是如果行为人盗窃的是体积较大无法藏于身上的财物,那么这种无法藏身的财物仍然是门口检查的范围,未出厂之前仍不能认定既遂。类似的盗窃还有很多,例如发生在博物馆、展览馆内的盗窃。所以判断从被人管理的区域内盗窃财物的既遂与未遂,必须把盗窃对象的性质与该区域的管理控制程度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5.有价证券盗窃的既未遂。有价证券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记名或不挂失有价证券,如国库券、无记名股票等。其特点是义务人只对证券持有人负责给付义务,也就是“认券不认人”。这种证券其实可以视为货币,窃取了证券,也应意味着非法占有了证券上所记载的一定数额的财产,所以盗窃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证券的既遂未遂标准与盗窃货币类似,到手即为既遂。第二种有价证券是记名或可挂失的有价证券,如记名银行存单、汇款单、汇票、本票、支票等,其特点是义务人根据证券向证券指定的人负责给付金钱的义务,也就是“既认券又认人”。盗窃行为人盗窃得到这种有价证券后,并不意味着已经获得了对证券所记载财产的完全控制。如果行为人要进一步非法占有证券所记载的财产,就必须以权利人的身份去支取财物。所以,盗窃行为人盗得记名、可挂失的有价证券后,在冒名领取时被人发觉或在行为人冒领以前义务人挂失或在窃得有价证券后马上被人抓获等原因,导致行为人没能最终控制证券中记载的钱财,就属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具备盗窃罪既遂的全部要件,应构成盗窃罪未遂;如果盗窃行为人窃得记名、可挂失的有价证券后,顺利地支取了证券中记载的财物则构成盗窃罪既遂。
6.盗窃运输中货物的既未遂。在运输工具如铁路、汽车上作案的,一般应以货物脱离运输工具时作为既遂。如汽车在行驶中,盗窃人扒车行窃,只要将货物卸下车,即为盗窃既遂。在停留的运输工具内行窃,如有人监视、警戒的,脱离了监视、警戒区才能控制财产,因而应以盗窃分子将财产窃离监视、警戒区为既遂;没有监视、警戒的,以窃离运输工具为既遂。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要对被盗财物取得了实际控制即为既遂,至于控制时间长短不是影响盗窃既未遂的因素。例如盗窃分子进入商店盗窃,刚走出店门即被店主发现,就擒,人赃俱获。按控制说,控制时间无长短要求,盗窃分子盗窃财物已经走岀店外,理应是既遂。
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的还是公然夺取的。盗窃罪的隐蔽性与抢夺罪的公然性所针对的对象自然是相对于物主而言。如在公共场所扒窃,虽然周围的人都看到行为人的盗窃行为,但只要不被财物所有人发觉就行。这时行为人构成的是盗窃罪而非抢夺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尾随被害人到一条无人的小巷,当着被害人的面抢了财物就逃,行为人构成的是抢夺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庭:《从一起个案看盗窃罪的既未遂及与相关罪的区别》,载《刑事审判参考》2005年第5集(总第46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8页。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林燕盗窃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557号)
裁判摘要:保姆对藏于户主衣帽间的财物并没有达到事实上的足以排除被害人占有的支配力,没有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因此构成盗窃未遂;保姆房间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之一,对藏于保姆房间的财物也应认定为盗窃未遂。
(一)主人对房屋内的财物是否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区分盗窃罪的既遂未遂时点,国内外刑法理论争议较大,主要有接触说、转移说、控制说、失控说、失控加控制说等。我们认为,正确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应立足于犯罪构成要件,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充足了盗窃罪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对于盗窃罪这种典型的窃取型财产犯罪,当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实现了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目的时,就认定为盗窃既遂。这种既遂实际上也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即非法占有的实现。因此,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应是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判断标准,其中占有的内容、方式、程度是准确判断的关键所在。
刑法上的占有,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权,仅指行为人对财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这种支配具有排他性,尤其是排除了被害人对财物的事实上的占有可能,从而使行为人实现了对财物的实际上的控制。这种事实上的可支配或者可控制能力,在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时较难判断:一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比如上下级或者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二是特定场所。在后者情形下,除行为人直接接触并占有财物之外,多数情况下行为人首先将财物置放于一定可控制范围之内,然后才将财物转移实现占有目的,因此如何界定合理的、适当的可控制范围,成为实践中认定的难点。本案所涉的保姆在主人家中盗窃主人物品即是上述两种情况交叉的典型。
通常认为,有特定范围的场所,物主的控制能力及于该场所内任何地方,里面的任何财物都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物主对这些财物享有事实上的控制权。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人对屋内物品的占有便是典型例证,但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主人对房屋内财物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尚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房屋的功能、结构以及居住人口和规模等都发生着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居民住宅之外,还有像单元套房、豪华别墅等结构较复杂、功能较多的住所;居住人群中,除家人外还可能会有客人、保姆等不同身份的人。房屋规模不同,居住人口不同,尤其是对于那些较大规模的房屋,主人对家中财物虽然具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但事实上控制力所能及的范围却是有限的,如行为人将财物藏于屋中某个秘处,可以随时待主人不备将财物带岀,此时就很难讲主人对该财物仍享有绝对的控制力了。据此,我们认为,主人对屋内财物的合理控制范围,仍需要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并结合财物的性质、形状、运送难度、社会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对此,可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被害人是否已经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这是行为人实际控制被害人财物的前提。可借助财物的形状、性质、被藏匿位置等分析被害人查找到财物的难易程度,从而判断被害人是否仍然享有控制权。如果财物被藏匿得极其隐蔽,或是被害人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或是被害人很难查找的地方,即可认为被害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比如把被害人的戒指藏匿于卫生间的垃圾筒或者墙壁上的一个小洞,相反,如果藏于电视柜或者衣柜抽屉里,则是基于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都会翻找且很容易找到的地方,此时就可理解为被害人并没有丧失对财物的占有。第二,行为人能够对财物进行事实上的控制。在这里,行为人对窃取财物的处理方式,也即藏匿方式,必须足以确保(行为人)占有,始得成立犯罪既遂。也就是说,行为人占有必须具备一定的要求、条件,只有当这种占有已经达到充分、及时的程度才可以认为行为人已经排他性地控制了该财物。换言之,被害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并不直接导致行为人控制该财物,行为人控制财物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保证或者确保占有的有效性,即最终确保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顺利实现。至于何为充分、及时的占有,需要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判断方法是行为人是否很容易地实现对财物的控制。举例说明,行为人将窃得的戒指等小件物品放到一个废弃的花盆中,主人已明示要将花盆扔掉,此时行为人可以公然将财物通过花盆运送于房屋之外而不被任何人怀疑或察觉。综上,房屋的主人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对被他人偷窃并藏匿于屋内的财物享有支配和控制力,需要结合案情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二)保姆林燕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衣帽间及保姆房间属于盗窃既遂还是未遂?
1.对藏于衣帽间的财物是否构成盗窃既遂?
本案中,被害人支某的住所系一幢三层别墅,衣帽间设在三层,且支某与被告人林燕约定:“不需要打扫二楼卧室的房间,只负责做饭和打扫客厅卫生。”虽然支某并不常去衣帽间,但其对衣帽间的所有物品均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占有和控制力;虽然林燕对藏于此处的财物也进行了必要的包装和掩饰,但鉴于衣帽间的用途和位置,支某如努力査找是不难发现被窃财物的。况且,林燕只是负责打扫卫生,除了具备可以随意进岀衣帽间的便利之外,其对处于衣帽间财物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故林燕对藏于衣帽间的财物并没有达到事实上的足以排除被害人占有的支配力,没有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因此构成盗窃未遂。
2.对藏于保姆房间的财物是否构成盗窃既遂?
保姆房间确实不同于房屋中的其他地方,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主人房屋占有力的一种限制。但保姆房间毕竟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之一,保姆对该房间的有限的使用权不同于承租人的独立的占有权。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对藏于保姆房间的财物也应认定为盗窃未遂。理由如下:
第一,从是否可以排除主人找寻可能性分析,主人并未完全丧失对财物的控制。首先,被告人林燕将窃取的财物放在了保姆房间的写字台抽屉里,而没有放置于其他隐蔽场所或者一般人很难査找的地方。其次,林燕并没有对这些财物做精心的掩饰、藏匿或者采取任何其他的防范措施。或许林燕自以为保姆房间就是她的私人空间,主人不会随便翻她的东西,但是她应当预见并且已经预见到,如果主人房间内丢失了任何东西,她都会被怀疑并进而主人会在整个房屋内的任何可想像的地方查找,包括保姆房间。再次,由于保姆房间空间小、家具简单、物品少,客观上直接翻查是很容易找到的。事实上,被害人就是首先找到了保姆房间的现金和首饰。
第二,被告人林燕对财物的控制需达到充分、及时,方可实现非法占有。首先,林燕需克服房屋内现实条件的制约,如被害人和其他保姆的监督。林燕刚刚来到支某家中做家政工作,支某要求林燕“不需要打扫二楼卧室的房间,只负责做饭和打扫客厅卫生”,此时如果发现了二楼卧室的房间内财物丢失,进入该卧室的人就会首先被怀疑。而由于支某共聘用了3名保姆,保姆之间相互监督,林燕必须在不被同在此处打工的另外两名保姆发现的情况下进入该卧室。其次,被盗财物放置的位置应尽最隐蔽,不易被察觉,即便是被放在保姆房间,也应该是位于一个常人不会找到的隐蔽角落。同时,由于存在另外两名保姆的无形的客观障碍,林燕还必须将财物藏于不易被其他保姆发现的地方,因为一旦有其他保姆发现就会将事实告诉主人,在私人住所这样的封闭场所,主人仍然在事实上控制着财物,林燕是无法随意或者轻易将财物拿走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被盗财物放置的位置应当利于转移,并最终实现对财物的转移占有。行为人对财物的控制最终要体现在现实的可支配上。由于财物仍处于支某的住所内,支某对房屋的所有权部分地限制了林燕的控制力,因为林燕尚未将所盗财物转移出主人家,林燕的占有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无法随意控制和支配的状态下。而盗窃罪需要两个行为即窃取行为和占有行为(有时候会发生两个行为的重合)方可完全实现,窃取后的转移占有是使占有现实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被告人林燕对财物的控制具有临时性,并未实现有效的占有。一方面,林燕主观上并不认为此时的财物已经属于自己所有。林燕在庭审时供称:“取得财物后,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担心随时会被主人发现。”这种心理状态说明林燕充分意识到了财物仍然是在主人的房间,并没有脱离主人的控制,一旦主人发现财物丢失并查找,其盗窃行为很容易暴露;另一方面,林燕对财物的掌控时间非常短暂,也可间接说明其尚无法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林燕从9月8日起到被害人家中从事家政工作,短短三天时间内连续作案,从其取得财物到被害人发现财物失窃到案发也仅仅两天时间,足以说明林燕根本没有实现对财物的控制。
第四,实现量刑公正、均衡的必然要求。如果林燕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既遂,由于盗窃财产数额已经超过10万,属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根据刑法规定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显然超出了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量刑过重。量刑对于定罪具有一定制约功能,量刑的轻重应准确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本案中,被告人林燕系来沪打工人员,其本身对财物或者首饰的价值并没有一个真实、准确的认识;其利用工作之便顺手牵羊,取得财物后并没有及时转移或者藏匿于更为隐蔽的地方,也没有立即逃跑;财物最终都被找回,被害人没有受到财产损失;林燕对其盗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有认识,但对其违法性的后果未必有清晰的认识,或者说如果林燕知道自己偷了这些现金和首饰后可能会带来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其未必会铤而走险,上述事实均说明了林燕的主观恶性及其行为的客观危害都不是很大,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法院认定其犯罪未遂并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是适当的,实现了罪刑相当。
——《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3集(总第68集)

网址:最高人民法院:盗窃罪的既、未遂及与相关罪的区别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921231
相关内容
盗窃罪盗窃罪的赃物怎么定价
打击宾馆民宿偷拍盗摄 严惩窃听窃照犯罪分子 典型案例公布→
入户盗窃认定标准的综合判断
打击宾馆民宿偷拍盗摄严惩犯罪分子 典型案例公布
警惕新兴盗窃犯罪!扫了微信“付款”,却没收到钱
探究偷盗抵押豪车法律界定,揭秘犯罪后果与法律风险
宿舍内的“猫腻”!民警1天内破获盗窃案获赠锦旗
如何保护家人安全?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与实用建议
打击宾馆民宿偷拍盗摄!典型案例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