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克维茨
安妮·莱博维茨以女性视角和大胆创新的构图著称 #生活知识# #摄影技巧# #摄影大师作品集#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1970年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普通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教授。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有:《发明创造性——社会的美学化进程》(1995)、《美学与社会——社会学及文化科学领域的基础篇章》(2018)。获得2019年莱布尼茨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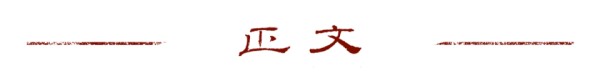
扁平的中产社会之后——晚现代的自我
后工业时代独异化经济的确立,以及数字文化机器的兴起,是晚现代独异性社会的结构性支柱。前三章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这一结构转型。本章中,我将探讨这一进程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即晚现代主体塑造生活的方式和主体被塑造的方式,以及这一点对整个社会景象的影响,就是说它如何在结构上影响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晚现代的自我与典型现代工业社会人格完全不同,这一看法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比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研究自我的自反性、风险意识和拼图人生;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分析,高度现代的自我是一种项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流动”的、以消费为导向的个人认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探讨晚现代生活方式,指出它总体上被灵活化了;还有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网络主体观点。我则认为,应该重新提出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与常有观点不同,我认为将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与这种生活方式主要的社会承载者群体分开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晚现代主体的最高形式,在社会结构上并不是空悬的,而是活动在可以清楚界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活动在一个社会文化阶级中:这就是新中产阶级。它所指的圈子,就是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化资本,大多具备高等学历,在知识文化产业中就职的阶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圈子。这个意义上的新中产阶级就是知识分子的圈子,是知识中产,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说到“承载者群体”,当然不是说文化化及独异化仅仅波及社会的某些特定部分和领域;这二者作为经济、科技以及价值转型的普遍进程,对整个社会和生活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主体都有影响。虽然影响有强有弱,但没有人能完全规避。只不过,独异化的生活方式最纯净的形式是存在于新中产阶层的。在这个阶层中,“创意圈子”又在起文化孵化器的作用,就是狭义创意产业(电脑和互联网、媒体、艺术、设计、营销等)从业者那种相对来说并不难懂,但文化上又很强势的生活天地。知识中产阶层——特别是在受到创意圈子的启迪之后——在晚现代社会中,全面彻底地致力于生活方式的独异化和文化化,他们是这一进程的先行者。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人与“文化”的关系、对独异性的价值理解和体验都是起引导作用的。“真”、实现自我、文化开放和多样性、生活质量和创造性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参数。这种生活方式还超越了其最初承载者的范围,获得了更强的影响力,变得唯我独尊。知识分子、拥有大学学历者和高端人才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起,渐渐地不再是一小撮精英,而是占据了西方社会——以继续增强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就是新中产阶级。
除了中产阶级之外,还要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它在根本上对整个独异性生活方式的影响。晚现代社会(又)成了阶级社会。阶级却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其实是不同的文化阶层:除了物质资源(收入和财产)的不公平分配之外,阶级也因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文化资本而存在根本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经历了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可以说是从扁平的中产社会向文化性阶级社会的转型。考虑到社会学界,尤其德国社会学界的基本观点,这一诊断乍一看会让人吃惊。在这方面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看法有代表性,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就是原有的社会政治大群体——阶级和阶层——被个人化取代的过程。与此相应,文化社会学家也认为,晚现代社会多种平等的生活方式并存。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生活方式和个人可以不受摆布地流变只是一种视觉假象。我们现在才慢慢感觉到,晚现代社会的文化化和独异化并不标志着阶级社会的终结,而是一个新阶级社会的开端。
工业化现代如今已成过往,它倒是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向着无阶级社会发展。不仅从现实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这样的,在西方它也是如此表现的,赫尔穆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将之精准地描述为“扁平的中产社会”。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三十年”是它最典型的阶段,美国、联邦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最为清楚地体现了中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扁平的中产社会与工业社会和大众文化(及其大众媒体和大众消费)相适应,也与政治的“社会民主共识”相适应。就我们对普适性逻辑和独异性逻辑的区分来说,可以断定:不仅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连扁平的中产社会都是彻彻底底属于普适性逻辑的,即以资源标准化、生活方式正常化为特点。这里的“中”不仅指社会统计数据的平均值(90%以上的人口达到了这个平均值),还表述着一种以“持中并标准”自居的生活方式:正常的劳动关系、正常的家庭、“正常”而适宜的消费等。扁平中产社会生活方式的核心,就是追求我们上文说过的“生活水准”——适宜的,但看上去总体正常的资源配备,对所有人来说,这意味着相差无几的舒适生活。

赫尔穆特·谢尔斯基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谢尔斯基主要研究德国战后社会:制度、分层、家庭、工业、青年、教育、失业和性。他是应用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青年成为了他所说的“怀疑的一代”,这种情况是由于国家的法西斯历史造成的,而青年们想要压制这种历史,因此这一代人主要关注职业和家庭生活。谢尔斯基晚年成为了一名律师和反社会学家。[图源:sociopedia]
文化性阶层分化与“料斗电梯效应”
自20世纪80年代起,扁平的中产社会与工业社会一同消亡,新的阶层分化逐步取而代之,这一清晰可见的阶层分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文化的。观诸西方社会,这一转型在美国最为剧烈,也影响了英国、法国,还有——程度稍弱,但也很明显——德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既涉及社会高层,也涉及低层。以前的中层削弱了,越来越显示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一个高端文化阶层,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本(以及中等至雄厚的经济资本);一个低端文化阶层,占有微薄的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本。一极是新中产,另一极是新底层。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美国发生的这次社会转型,即中产社会转向两极分化,其典型的社会性特征对于整个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总而言之,扁平社会的标志是收入相对公平,以及包括普通工人和职员在内的普遍富足。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同时,要获得中产身份,正规学历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居住区相对混杂,却又有统一性:混杂了各种职业,但他们实际上过着同样的中产生活。人际关系——包括婚恋关系——也常常跨越职业群体和学历水平的界限。
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环境整个变了。已经能明确说出社会文化两极分化的承载群体:新中产,拥有高学历,多为大学学历;与之对立的是新底层,学历较低(或没有正规学历)。它们之间,是旧有的非知识中产。2000年以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都在关注社会不公的尖锐化,特别着眼于占人口1%而拥有巨大财富的“顶尖富人”。其实对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整体文化来说,占人口大约三分之一的新中产阶层更加重要,更有影响力。新中产阶层的扩大,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进程:一个是前面说过的经济结构向后工业时代转型,其结果是高端知识文化类职业领域的扩张;另一个是教育的普及,使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大学学历者增长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新知识阶层崛起的反向,是新底层的形成。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是最早研究新底层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简单服务业的扩张和新的低学历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的扩大,也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新底层总体上是杂糅的,包括简单服务业从业者、半专业的工种、重体力劳动者、失业者和社会救济对象(也包括真正意义上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现在大约占西方社会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收入、财产和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以前的中产水平。这个阶层产生的社会原因与新中产产生的原因正相反:后工业经济转型意味着产业工人阶层(包括一部分工作固定程式化的普通职员)在快速消失。同时,直接或间接受益于新兴知识文化产业或新中产阶层需求的简单服务业人群,其重要性在迅速提高。教育普及对新底层的形成也有反作用:没有被教育普及包括在内的人,成了“教育失败者”,因为专业能力弱,他们能从事的工作,只剩下在经济文化意义上属于服务阶层的那些了。

Gøsta Esping-Andersen,丹麦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福利国家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十年中,他的研究转向了家庭人口问题。他的研究综述出版了《21世纪的家庭》。[图源:Wikipedia]
晚现代生活方式的两极分化,涉及物质和文化两方面。从物质层面来说,以前相对公平的收入和财产分配模式被一种复杂的变化取代了。新底层的财富紧缩前所未有,这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跌出了中等生活水准,也使他们经常处于困难的从业状况中。而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较小:新中产的上层——知识产业从业者,从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获益的人——的经济资本在增长,同时,知识中产与原有的中产阶级相比整体上至少保持了稳定,只是其中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情况不太稳定。然而,总体上还是可以断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收入剪刀差明显扩大了。所以,两极分化也是物质层面上的。
将知识分子阶层连成一体的纽带,使他们拥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其实是他们雄厚的文化资本。总体上说,教育和文化资本的两极分化才是晚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扁平的中产社会,是否拥有毕业文凭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过上中产生活;而在晚现代社会,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对立却对社会结构有决定性的作用;对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正是个人的“教育因素”。对社会分层极为重要的“教育”,包括学历,也包括非正式的文化资本。教育历程的分化,与教育流动性的降低是联系在一起的。阶层两极分化也体现在居住上。城市里就很明显,以前中产混居的社区消失了,分化成了知识分子居住的“魅力社区”和新底层居住的“问题社区”。在空间上也相应地出现了热点地带和“脱钩地带”的两极分化。所以不足为奇,跨阶层的人际关系(包括广义上的家庭)以及婚恋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比组织化现代社会中的有了明显减少。
除了严重两极分化的新知识中产与新底层之外,晚现代还有两个重要阶层,在这里至少要先简短提及:社会顶层以及“旧”中产即非知识中产。它们补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图景。积累了极大财富的社会(新)顶层,是独异性经济(比如在金融、体育、管理等领域)赢者通吃的必然结果,他们与新中产的显著区别,更多地在于经济(及社会)资本而不是文化资本。只要有了足够的经济(及社会)资本,通常就可以不受劳动收入的限制,将有创意的生活方式升格为奢侈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由非知识分子构成的旧中产,是以往扁平中产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直接后裔。他们的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规模中等,可以保证中等的生活水准和一般认为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新的知识中产是晚现代阶级社会最上层的三分之一(包括数量极少的顶层),新底层是最下面的三分之一,旧中产就是居中的(趋于缩小的)三分之一。晚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三分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降,旧中产从物质层面,尤其从文化层面上来说都在沦于被动地位。它不再是引领者,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上无可取代的中流砥柱,而是卡在新知识中产和新底层中间,而且成员还在不断向两边流失。看似正常的中产生活方式不再适用于所有人,不再是“持中并标准”,而仅仅是“中不溜”:一边是知识阶层独异化生活方式的繁荣,另一边是“脱离社会”的新底层的迫近。
审视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业化现代典型的“扶梯效应”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增加财富;晚现代的社会与此相反,其结构的典型特征,我想以“料斗电梯效应”来描述。扁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并不相同,却多多少少还有可比性,而且文化生活方式相差无几,社会这个“料斗电梯”两边的轿厢还处于差不多的高度上。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一个社会群体的轿厢向上,即新的知识中产(包括新顶层),另一个群体的轿厢向下,即新底层(包括一部分非知识中产)。如果只将注意力放在收入和财产上,是无法理解料斗电梯效应的。当然,电梯的升降也包含物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社会各领域的文化化,也决定了生活方式和阶层分布。所以,料斗电梯效应也包括,而且特别是指社会各阶层文化意义上的上升和下降过程。
新中产在文化意义上的上升以及新底层(包括部分旧中产)的下降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文化资本。高等学历和非正规文化资本都是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自我价值的关键资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高学历的新中产就会“步步高升”,而其他人,尤其是学历低而且非正规教育资本少的人就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在扁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普通学历也能带给人机会,是“正常一般水平”,而现在持这样学历的人成了“低水平”的人,能得到的机会非常有限。
第二个层面是自我文化化的生活方式。这是新中产的标志。新中产对世界和自我的关系,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大同主义的文化观体现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全面审美化和伦理化,追求实现自我,实现“真”。这种独异化的生活目标,除了追求生活水准之外,还有一层文化上的价值,即生活质量和“美好生活”。正是这种生活质量为新中产带来了社会名望。与之相对,生活艰难的新底层不太可能进行文化化,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持正常生活、满足基本需求上。他们有一种“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态度,只够用来对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在扁平的中产社会中,人们关注生活水准和保障,与此相比,新中产阶层文化化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而且要求更高(上升),而新底层的生活方式则根本不能满足以往的要求(下降)。
第三个层面是阶层之间鲜明的赋值和去值过程。如果强意义上的文化意味着区分价值与无价值,那么赋值与去值进程就是晚现代阶层结构的根本。新中产的生活方式被整个社会推崇为“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承载它的主体就是有价值的主体,具有宝贵的品质(创造力、开放性、自我意识、企业精神、同情心、大同主义等)。因而可以认为新中产主体承载着开创未来的生活方式,这也成了衡量生活圆满成功的社会准则。而新底层(其实也包括旧中产)的生活方式则被看作缺少价值的、有缺陷的,这不仅体现在主体的自我认知上,也体现在他们的社会表现上;新底层的生活方式是负面文化化和去值的对象。底层这个称号就说明,它在外人眼里和自己眼里,都是处于社会等级下层的——被看作“失败者”和“脱离社会者”的文化。“不平等”在这里经历着文化化。这就是说,在社会表现和主体自己的认知中,不平等都不再指物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能力、道义,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价值或无价值。
综上所述,晚现代社会结构的料斗电梯效应,是由以下因素产生的:新中产对生活方式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一种令人满足同时又成功的“美好生活”,这种资源雄厚、获得赋值的生活方式在上升;同时,新底层资源匮乏,生活方式又遭遇去值,连较低的生活要求也难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在下降。扁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承诺,让所有人过上较为舒适的中等生活;而晚现代独异化的生活方式虽然是整个社会的榜样,被所有人向往,社会却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得到它。

〇本文节选自[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第五章“独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阶级、主体形式”,巩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因内容较长,故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文化资本。[图源:comstocksmag.com]
〇编辑 / 排版:彭彭 / 山本木子
免责声明:本内容来自腾讯平台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或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举报
举报
网址:莱克维茨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985860
相关内容
【先刚】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合肥伊莱克斯空调维修加氟电话=合肥伊莱克斯空调统一服务热线
【伊莱克斯 CXW
莱克吸尘器使用说明 莱克吸尘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2024年伊尔库茨克旅游攻略
莱克挂烫机怎么样 莱克挂烫机价格
维茨金的学习艺术
【伊莱克斯电器】品牌介绍→伊莱克斯厨电
莱克智生活app
编程祖师爷尼古拉斯•威茨:算法+数据结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