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的“有人美学学派”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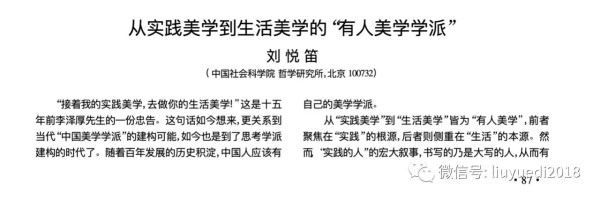
“接着我的实践美学,去做你的生活美学!”——这是十五年前李泽厚先生的一份忠告。这句话如今想来,更关系到当代“中国美学学派”的建构可能,如今也是到了思考学派建构的时代了。随着百年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美学学派!
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皆为“有人美学”,前者聚焦在“实践”的根源,后者则侧重在“生活”的本源。然而,“实践的人”的宏大叙事,书写的乃是大写的人,从而有别于“生活的人”的小写言说。李泽厚本人是肯定以“生活美学”和“环境美学”为代表的“有人美学”的,而否定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为代表的“无人美学”的。
近期引发了对李泽厚先生这种区分的集体反驳,大家都是在说我们也是“有人美学”!我的再反驳是:有人与无人其实是就整体哲学与美学趋向而言的,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态,当然是走“自然化”道路,无论是人性的自然化还是自然的生态化都是此路,哪个美学不是“属人”的呢?!
与“有人美学”之道殊途,一面是倡导生命与超越的美学(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后来也生发出“生命论”趋向),另一面则是崇尚生态的美学(蔡仪的客观论美学早有“以自然为中心”的取向),它们之所以是“无人”的美学,因为前者落归于动物生命,后者认定自然为中心,由此这些美学趋向都是“去人化”的。反之,以“生产形式”为基础的实践美学与以“生活形式”为基调的生活美学,都可归属于“有人美学”一派,二者皆是建基在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基础之上。
随着百年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美学学派”,而“有人美学派”可以在其中位居主导之位。因为各种后实践或者实践之后的美学形态,都是将实践美学作为批判靶子,无论是以生存或生命替代实践本体,还是将实践与存在论接通起来,从“生产美学”与“存在美学”便构成了两极,这是“实践-后实践”的理论范式。“生活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是内在传承且和而不同的。
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走的还是自然人化抑或客观社会化之路,这是一脉相承的。常有人误解:生活与生命、生存、生态,这几“生”是不是非常接近?实际上,生活与实践更接近,而生活离生命、生态其实更远,而有着本质性的区隔:那就是以“有人”为内核还是以“无人”为核心。
英文life与德文leben并没有区分出生活与生命之义,但希腊文中,这个词却被泾渭分明的区分开来:一个是zoē,乃是指一切活着的存在(动物、人或神),他(它)们所共有的简单存活事实,接近于汉语的“生命”或“生存”之义;另一个则是bios,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的适合之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接近于汉语的“生活”之义,“生活美学”取后者之义。
生活更强调“生”的社会意义和“活”的文化价值,生“命”则更接近生理维度,这就是生之“命”与生之“活”的基本区分。活更多强调的后天的人化维度:生是自然的,而活则是不自然的。
生活,乃是自然的生与不自然的活的合一,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更强调自然人化,强调后天的要素。伦理也是如此,后天教化一定重于先天积淀,尽管人类审美当中的先天积淀更多一些,但这的确是“经验变先验”,那些看似先天的东西其实大都也是后天积淀而成的,审美与伦理乃是遵循同一历史进化规律的。
当代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从共和国建立那时算起,应该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在生活》——这个生活,有接近生命的意味。或者说,生活当中包孕了生命的基层意义,生命是生活的基础层,有时用语干脆的就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中译本当中的“生活力”的概念,其实应为“生命力”,但是美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生命”,而是“应当如此的生活”。
我以为,“美是生活”是上世纪中叶中国美学界集体服膺的美学基本观念,李泽厚也较早使用了“生活实践”这个术语,后来才将实践独化出来:“当现实肯定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时候,现实对人就是美的”,生活论这是李泽厚美学的内在源泉。
李泽厚这一辈还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中不仅有费尔巴哈提纲的影响,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李泽厚在巴黎手稿中做过大量的批注,手稿当中的关键之处,的确是李泽厚“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观念的基本来源。
“美学大讨论”的四派论是蒋孔阳先生率先归纳出来的,李泽厚则不承认主观派而认定只有三派,但其实更应归入两派:蔡仪的“自然派”与李泽厚“社会派”。这与前苏联两派美学论争是异曲同工的,但是中国人的创建还在于提出了实践论。如今看来,“社会派”一脉乃是“有人美学”,而“自然派”及“主观派”的另一脉则是“无人美学”,这个历史线索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
我受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theory)、实践(praxis)与创制(poeisis)的三分法的启示:与理论相对,广义的人类活动或人类的做,可以区分为poiesis与praxis两类,但西方思想界却不仅以praxis遮蔽掉了poiesis,且将work乃至labour提升为超越praxis的地位之上。但美学的根基,并不在于praxis那种有意志的实践行为(willed practical activity),反而更在于poiesis之“生—成行为”(pro-ductive activity)。
实际上,美学的根源不在praxis,而在于poeisis,因为这个词不仅与诗学非常近似,本身就有审美内涵,而且它的创生的含义就不是生产的那种基础意义。我认为,美学与哲学的“做”的根据都在于此,这可用庄子庖丁解牛来进行阐释,这个审美化的过程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创制创生。实践的始基还在劳动,但是生活的根源则在创制与创生。美不是生产或实践,而是创生化地做,而不是生产性地做。中国本土的哲学与美学,由于对“生成”(becoming)与“创生”的眷恋,而非对“存在”(being)的执著。
“生活美学”与李泽厚先生所创生的“实践美学”,其根本差异就在于,后者是建基在praxis之上的美学,前者则是建基在poesis之上。当李泽厚把praxis被狭窄为labor的时候,也一定要意识到,它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的根据,生存需要劳作,但是生活却另有其根。人类的“生—活”,以实践为根基,但生活并不是实践本身,生活反而是“生—成”的活动。
这poesis,一方面关注对生活之“创生”,并以坚实的“创制”活动为底蕴;另一面也强调生活本身的“创造”,以真善美合一的“生成”作为理想态。所以说,“生活美学”之生活,本就是一种创生性与创造性的生成活动,而绝不能等同于劳作那种生产。质言之,广义的“做”,既包括praxis也包含poiesis,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不仅仅是实践的传统,而且更是生成的传统,后者才是“生活美学”之人类活动论根基所在。
我所谓的“生活美学”建构的基本诉求是,第一,作为哲学美学,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当然是首要的。第二,作为本土的美学,如何将这种美学回归古典美学当中,也能得以系统化的呈现。第三,作为体用不二的美学,如果在生活当中普及,回归生活引领生活。美学在中国恰是一种幸福之学,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就是这条路数。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理、情感到文化的各个层级上,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将“过生活”过成了“日日皆美日”。
总之,关键是美学可不可以化入生活,所以才成为生活的美学。与李泽厚先生的私下对话当中,我曾先说,可惜实践的美学不是美学的实践,李先生马上回我:实践美学就该是美学的实践,那么,同理可证,生活的美学也应是美学的生活!
我认为,如今中国美学学派的建构是可能的,它要继承两千年来中国古典美学“人能弘道”的儒家主流传统,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实践美学“实践成人”的现代传统,新世纪开始以反本开新形式出场的“人归生活”的当代传统,由此方能形成“中国美学学派”得以延承的历史积淀,从而面向未来积极拓展,最终立足于世界美学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