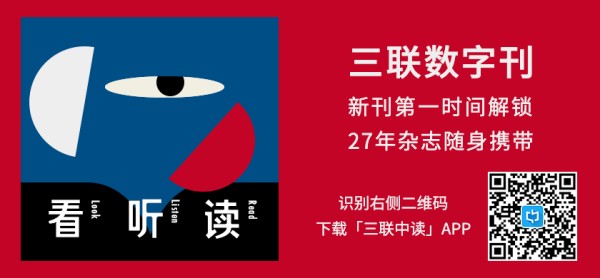“德彪西毫无创新,是萨蒂不断冒出新点子——他从火中取栗,德彪西再把它们卖给公众并从中渔利。”
而他的音乐完全不像他那么凌乱,竟是异常清澈悦耳的。至今流传甚广的主要是萨蒂的钢琴曲。这些钢琴曲清冷唯美,几乎找不到传统的依据,他的源头不是肖邦、李斯特,而是酒馆里的流行歌曲加伴奏的卡巴莱。他固执,眼光高,只取精髓,看不上音乐学院教授的一切模式。因此他的作曲方法就像“搭积木”,一段叠一段,连衔接都不给。以模仿哥特建筑而作的《拱形》,所有的和弦孤单耸立,乐谱笨拙得像和声作业。他的成名曲《裸体舞曲》和《玄秘曲》也是如此,仅一两种伴奏音型一径轻盈到底。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被当做流行乐手。因他想法独特,文艺得高端,忧郁得艺术,连酒馆的轻音乐都能被他弹成一曲曲素歌。
看看标题你就知道他有多纠结了。没有人像萨蒂那样,靠着标题就能出名:《裸体舞曲》、《冷曲》、《运动与嬉戏曲》、《牙疼的猫头鹰》、《脱水的胎儿》、《非宗教而华丽的诗》、《恶心的附庸风雅者的三首优雅圆舞曲》,还有题献给狗狗的前奏曲。他热衷意象混搭,捕捉幽微莫名的情绪,变奏熟悉的乐曲来插科打诨,而且貌似一个未被发掘的诗人。但怪诞的曲名不曾打搅他冥思般神秘的音乐。《裸体舞曲》听得人迷惑,这多美啊,飘渺,抑郁,泛着泪光,一点也不色情啊?你一定想不到,萨蒂想要表现的是裸体的羞耻感,他在乐曲中引用了一段西塞龙的句子:“我们的传统道德禁止发育成熟的年轻人在洗澡时一丝不挂,这样,耻辱感就在灵魂深处根深蒂固了。”等你把这些乐曲的附文读一遍,会发现他其实还是一位有点做作的思想家。
1917年,战争之后,人们不再记得印象派的良辰美景了。此时萨蒂开始时来运转,他遇见了戏剧,遇见了毕加索。《游行》和《苏格拉底》的成功与毕加索的加盟不无关系,虽然毕加索和萨蒂在生活中不曾交集,但他们作品中对简洁质朴的艺术追求非常一致。《游行》的功劳来自毕加索和科克托。这又是一场酒馆合作。26岁的才子科克托一直在蒙巴那斯的酒馆和咖啡馆与诗人、野兽派艺术家们交游,立志倡导现代主义。有一天,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大人物佳吉列夫跟他说:“做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吧。”他忽然就有了灵感,想写一部马戏芭蕾,即在芭蕾舞中穿插马戏团的小丑和杂技表演。《游行》的情节很简单,只是一场马戏表演,但又不只是马戏与芭蕾,它流露出马戏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毕加索的舞台与服装设计非常成功,色彩暗淡,线条逼真突露:现实中昏睡的狗,想象中飞翔的马,猴子在云梯上四处张望,场景已经充满暗示。据说《游行》的成功在当年可以和《春之祭》相提并论。从这部剧中可看出,萨蒂心目中的戏剧音乐首先是一种配乐,他采用短小曲调和舞曲片段做背景在《游行》中反复始终。因剧情需要,萨蒂在音乐中加入了打字机、摇奖器和汽笛,这让他又一次引领潮流。
《苏格拉底》是一部严肃的由对话组成的抒情交响乐,取材自萨蒂最喜欢的柏拉图的著作《对话篇》。全曲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长篇大论的《苏格拉底素描》,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的《伊利苏河边》,一段《苏格拉底之死》的宣叙调。音乐跟随剧情从喧闹流向平静与纯洁。《苏格拉底》体现了萨蒂的多重自我的汇集与提炼:他对质朴的古代生活的向往,对苦行哲学家的崇拜,对虚无的迷恋,他的音乐向往“与古代一样洁白纯净”。可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当身穿督政时代的洁白长裙的夫人们,每人手执一卷《对话篇》,唱出纯洁、高亢、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声,竟把台下逗得哄堂大笑。不管怎样,萨蒂因此受到了《新法兰西》杂志的吹捧,从酒馆小市民一跃成为巴黎的上流知识分子。
萨蒂在这出《苏格拉底》中开创了“室内装饰音乐”,即剧中运用的背景音乐,有“挂毯前奏曲”、“浮雕主题”和“浅浮雕首饰匣主题”等等。这些配曲和剧中的类似格里高利圣咏的宣叙调相距十万八千里,就像马赛克配上波斯花纹,乱中有序。他擅长捕捉混搭的妙处。后来萨蒂另做了一次“室内装饰音乐”的实验,他要求听众随心所欲地聆听、踱步,发表意见,好像音乐不存在。这个想法后来在“简约主义”音乐中被广泛展开。
如今听萨蒂,听过你就会明白过来,眼下时髦的混搭和闷骚其实他在100年前早已玩过了。也许我们没怎么听说过萨蒂这个音乐家,但一定在广告中、在电视节目的片头听过他的乐曲,如今他的音乐被广泛用作配乐,用作背景音乐。正如他早已预见的背景音乐的前途。但他的音乐特征已发生了演变,他不再局限于法国了。他的钢琴曲出现在美国电影、日本广告中。在韩国电影《撒玛利亚女孩》里,它象征了美好的信仰与人性幽微;而在英国电影《面纱》里,它变成一缕发黄的怀旧气息。如今听来,萨蒂的乐曲仍然适合酒馆,不过是有留声机和狐步舞的尘封的小酒馆。
168